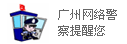二十三年前已經(jīng)終審的傷害案再次起訴追加賠償法院應(yīng)否受理
[案情]
1981年1月27日上午,于青和楊海燕結(jié)伴給同學(xué)楊靈送成績單。來到楊靈家后,三位同學(xué)愉快地交談著期末考試的情況,談話間于青發(fā)現(xiàn)楊靈的寫字臺上擺放著一支手槍,便好奇地拿起來玩耍,她一不小心扣動了扳機,只聽“砰”的一聲,子彈穿出槍膛打穿了楊海燕的脖子,楊海燕應(yīng)聲倒下,鮮血從傷口汩汩流出。伴著楊海燕凄厲的哭聲和痛苦的掙扎,于青和楊靈霎時蒙了。他們一邊打電話叫人,一邊手忙腳亂地照料著楊海燕,并協(xié)助醫(yī)護人員把她送到海軍401醫(yī)院救治。
原來,楊靈的爸爸是海軍現(xiàn)役軍人,他把所配的手槍放在家里。事發(fā)那天,楊靈找到爸爸的手槍玩耍,把子彈推進了槍膛。于青拿起手槍玩耍時,楊靈沒有及時提醒和制止,于青誤認為手槍里面沒有子彈,在隨意撥弄時導(dǎo)致手槍走火。
楊海燕住院近一年后出院,被醫(yī)院確診為:頸部貫通傷,第一胸椎開放性骨折,并脊髓損傷,高位截癱。
1981年9月19日,青島市市南區(qū)法院分別判處兩被告人構(gòu)成過失傷害罪,但考慮到兩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及三名同學(xué)關(guān)系良好等從輕和減輕情節(jié),對兩被告人免予刑事處分,并各賠償受害人人民幣5000元。判決后雙方當(dāng)事人均對民事判決部分不服,原告以判決數(shù)額過低、而兩被告則以數(shù)額過高為由提出上訴,青島中級法院于同年11月18日做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隨后兩被告人繳清了應(yīng)付款,該一萬元賠償款中,包括受害人在醫(yī)院實際支付的治療費2000元。
此后楊海燕的父親以賠償數(shù)額太少為由上訪申訴,但無結(jié)果,直至2004年9月21日市南法院受理此案。這樣,楊海燕以原告身份,在事發(fā)23年之后,再次將于青、楊靈及他們的父母共六人告上法庭,要求賠償后續(xù)護理費、輔助用品費等共計人民幣40多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多元。
原告訴稱:被告于青是直接加害人,被告楊靈疏忽大意將手槍子彈上膛并擺放在桌子上,在于青玩弄手槍時不予制止或提醒,對原告的傷害后果具有間接過錯。兩被告的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人應(yīng)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特別是被告楊靈的父親,其未按槍支管理規(guī)定保管槍支,也是原告受到傷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被告應(yīng)依法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
被告的行為對原告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而且持續(xù)時間長。自16歲受到傷害后,原告的正常生活自此嘎然而止,每日遭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和折磨,自己連最低的生存需求都難以自理。更加遺憾的是,原告的父母幾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對原告的照料中,還將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原告的生活和殘疾用具支出。現(xiàn)他們已經(jīng)年逾古稀,還要為孩子的未來焦慮和擔(dān)心,忍受著生活的巨大壓力;而原告不僅不能侍奉父母,相反,還處于未來父母故去后自己將陷入無人照料的恐懼之中,常常感到生不如死。
1981年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盡管已判決被告賠償一萬元,但此款扣除醫(yī)院的實際支出 2000元后,所剩8000元與原告的實際花銷相比簡直杯水車薪。現(xiàn)原告已經(jīng)陷入生活的困境,該困境是由被告造成的,因此與情于理于法,被告都應(yīng)當(dāng)繼續(xù)給予賠償,以使原告能夠繼續(xù)生活下去。
被告于青和楊靈辯稱:我們承認給原告造成了傷害和痛苦,但事發(fā)之后,我們?nèi)f(xié)助救治,并依法院的裁決承擔(dān)了刑事責(zé)任和民事賠償責(zé)任。法院判決的賠償數(shù)額,在當(dāng)時是很高的了。同時,法律的基本原則是“一事不再理”,此案當(dāng)時判決時并未確定賠償年限,是一次性賠償,現(xiàn)在原告要求追加賠償違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再者,原告與我們的糾紛已經(jīng)過了23年之久,法律規(guī)定,身體受到傷害的訴訟時效是1 年,在此期間不主張權(quán)利則會喪失訴權(quán);即使按照最長時效20年來計算,原告的起訴也超過時效了。因此其不僅失去了訴訟上的權(quán)利,也失去了實體上的權(quán)利,因此應(yīng)依法駁回其起訴。
上述兩被告的四位家長的答辯意見也比較接近,他們除重申了以上意見外,還辯稱:事發(fā)當(dāng)時,上述兩被告是未成年人,我們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監(jiān)護責(zé)任,并因此代孩子賠付了原告各5000元,現(xiàn)在他們已是成年人,我們作為監(jiān)護人的資格已經(jīng)消失,把我們列為被告是主體資格錯誤,要求駁回原告對自己的起訴。
法院查證的事實與雙方當(dāng)事人陳述的事實基本一致,出入不大。雙方的爭議主要不在于事實的爭議,而在于在此事實的前提下,該做出怎樣的法律評價和承擔(dān)怎樣的法律后果。為重新確定原告現(xiàn)在的病情,受案后,市南法院委托有關(guān)鑒定部門對原告的病情重新作了法醫(yī)鑒定。結(jié)論為:被鑒定人楊海燕槍擊傷后經(jīng)醫(yī)院檢查其見有頸7胸1椎板骨折、頸髓貫通傷并高位截癱等損傷。雖經(jīng)治療,現(xiàn)其傷情并無明顯改善,仍遺有高位截癱、大小便失禁和雙手大部分功能喪失的表現(xiàn)。根據(jù)以上情況,參照《職工工傷與職業(yè)病致殘程度鑒定》之規(guī)定,認為,其損傷目前已達一級傷殘標準。同時市南法院還根據(jù)原告的申請,委托中國康復(fù)研究中心附屬北京博愛醫(yī)院對原告需要的殘疾人用品等各項支出作了評估,并給出了詳細結(jié)論。
[審判結(jié)果]
法院于2005年8月15日做出一審判決。法院認為,本案的傷害事故發(fā)生在1981年1月27日上午,至今已24年。當(dāng)時雖經(jīng)市南區(qū)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由被告于青和楊靈之法定監(jiān)護人各賠償原告人民幣5000元,但該筆賠償款顯然已經(jīng)遠遠不能繼續(xù)維系原告基本的生活需求。2004年5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二條規(guī)定“超過確定的護理期限、輔助器具費給付年限或者殘疾賠償金給付年限,賠償權(quán)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繼續(xù)給付護理費、輔助器具費或者殘疾賠償金的,人民法院應(yīng)予受理。賠償權(quán)利人確需繼續(xù)護理、配制輔助器具,或者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判令賠償義務(wù)人繼續(xù)給付相關(guān)費用五至十年。”這一規(guī)定明確了一次賠償可以多次請求的原則。該人身傷害案當(dāng)時的判決盡管沒有明確認定是二十年的賠償款,但事實已經(jīng)證明原賠償款遠遠不足原告的實際支出,原告再次起訴要求賠償,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確定的賠償原則,因此原告有權(quán)再次起訴要求被告賠償損失。
原告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實施之后再次起訴要求后續(xù)賠償,是現(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生并繼續(xù)發(fā)生的損失,不存在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因原告要求的賠償款是其以后生活的費用,所以,亦不適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則,被告的此種抗辯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事故發(fā)生時,被告于青及被告楊靈未滿十八歲,不能獨立承擔(dān)民事賠償責(zé)任。現(xiàn)被告于青及楊靈已成年,基于未成年人的替代賠償責(zé)任條件已不存在,對于給原告造成的傷害,于青的父母不再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被告楊靈的母親亦不應(yīng)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被告楊靈的父親楊某違反武器保管規(guī)定,對于事故發(fā)生負有重要責(zé)任。因此,對于本案確定的賠償金,應(yīng)由被告于青賠償百分之五十,被告楊某和被告楊靈共同承擔(dān)另外百分之五十。
被告的行為確實給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但是根據(jù)法釋[2002]1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fù)》規(guī)定,在本院已作出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之后,原告再提精神損害賠償已無法律依據(jù),因此,對原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shù)脑V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二條之規(guī)定,判決被告于青及楊靈和其父楊某共賠償原告殘疾賠償金、護理費和殘疾輔助器具費共計人民幣40多萬元,其中,由被告于青負擔(dān)百分之五十,被告楊靈和被告楊某負擔(dān)百分之五十。
[分析]
由于本案時間跨度較長,因而衍生出很多法律問題,包括訴訟時效問題、訴訟上的“一事不再理”問題、《最高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是否適用于該案的問題、被監(jiān)護人造成他人傷害在其成年后其監(jiān)護人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問題,甚至還涉及情與法以及法律公正和樸素正義的關(guān)系問題等。
訴訟時效制度,是指法律主體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quán)利被侵害后,應(yīng)當(dāng)在什么時間起訴請求法院保護、過期則失去訴權(quán)的制度。這個時間的起算點是從他知道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自己的權(quán)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一般的訴訟時效期間是二年,有的是一年,還有的是三年。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主要由兩個,一是督促權(quán)利主體盡快起訴,避免權(quán)利的歸屬處于法律上的不確定狀態(tài),影響社會財富的穩(wěn)定和合理配置。二是當(dāng)事人不趕快起訴,不僅使案件事實不便查證,給法院審判帶來困難,而且可能因為社會生活的變動使判決變得沒有必要。訴訟時效制度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在于:為了保證法律規(guī)則體系的周延運行,需要對樸素的社會正義進行規(guī)則性地合理取舍。
“一事不再理”原則是指,同一法律爭議在法院作出生效判決以后,不得在這一法律結(jié)果上再疊加另外一個結(jié)果。“一事不再理”原則有別于上訴審,上訴審是一審判決未生效時啟動的二審程序:“一事不再理原則”也有別于再審程序,再審程序是指已經(jīng)生效的判決發(fā)現(xiàn)錯誤或因出現(xiàn)新的證據(jù),通過再審改變原判決的審理程序。再審程序指向的是對原判決的變更,使原判決的效力解除。
最高法院于2003年12月26日公布、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這樣一個原則:即一次性賠償不限于一次性請求。從立法本意上看,其適用范圍是指,對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殘疾者生活補助費都規(guī)定了20年的賠償期限,但判決以后,有些受害人在20年過后仍然存活,此時可再次起訴,法院可以再行判決5到10年的相關(guān)費用。
就本案而言,筆者從司法良知和社會樸素正義感的角度出發(fā),同意并愿意相信市南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理由如下:一般而言,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對民事賠償部分的審理一般是比較粗線條的,賠償數(shù)額認定雖不能說比單獨提起的民事訴訟所獲賠償數(shù)額低,但由于計算較粗,可能會遺漏某些賠償項目。本案81年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賠償數(shù)額也是這樣,盡管當(dāng)時判決賠付一萬元是不少的,但與一個16歲的少女終生癱瘓在病床上所支出的費用相比顯然是杯水車薪。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可能不被大多數(shù)人所想到,那就是這一萬元并不是要在81年那個物價較低的年代全部花掉,而是跨越了物價高的年代直至現(xiàn)在。而利息的增長遠遠低于物價的增長,當(dāng)時的一萬元慢慢花銷到后來的時候,其交換價值跟隨時間的推移逐漸貶值,因此難以繼續(xù)維持原告的基本生活。民事賠償?shù)幕驹瓌t是“填平損失”或叫“填補損失”,被告支付的一萬元賠償款,遠不足以“填平”或“填補”原告的經(jīng)濟損失和漫長的肉體和精神痛苦。從“矯正的正義”的角度,被告再行賠償理所應(yīng)當(dāng)。否則,原告的生活將無以為繼。
但若純粹從法律的角度來說,筆者認為本案判決的法律依據(jù)值得商榷。因為,81年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并沒有確定賠償款的給付期限,應(yīng)當(dāng)指的是一次性賠償,因此本案應(yīng)當(dāng)適應(yīng)“一事不再理”的訴訟原則。而《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前提是已經(jīng)確定了賠償期限的判決超過賠償確定年限的情況,因此適應(yīng)該解釋顯得有些牽強。同時,即使推定市南法院81年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確定的是對原告二十年期限的賠償(這個時間不應(yīng)以青島中級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時的時間為準,而應(yīng)自事發(fā)當(dāng)日時起算),那到2002年時已二十年屆滿,這個期間應(yīng)當(dāng)是除斥期間,不能延長。按照時效理論,原告受到的身體傷害訴訟時效為一年,到2004年原告起訴時已屆二年,也超過時效的規(guī)定了。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要支持原告的訴訟主張在法律上都是很勉強的。如果本案可以重新提起訴訟,照此先例,那將會使很多基于一次性判決生效的人身傷害案件重新啟動并進入訴訟程序,法院判決的既判力將受到威脅。
但是如果解除了被告的賠償責(zé)任,原告以后的各項支出應(yīng)該由誰來承擔(dān)呢?
另外,還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監(jiān)護責(zé)任是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子女和其他被監(jiān)護人應(yīng)盡的法定義務(wù),其所產(chǎn)生的賠償責(zé)任在損害形成時隨之產(chǎn)生,只能因履行等法定事由而消滅,不因被監(jiān)護人成年后而自然解除。因此,本案不應(yīng)解除于青和楊靈之父母的賠償責(zé)任,筆者認為,倒是于青和楊靈仍然不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應(yīng)由其當(dāng)時的監(jiān)護人即兩被告的父母承擔(dān)責(zé)任。
本案一審判決后,被告已經(jīng)提起上訴。但無論終審結(jié)果如何,這起案件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因為本案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協(xié)調(diào)社會樸素的公平正義觀和法律規(guī)則之間在個別案例中表現(xiàn)出來的沖突?這一問題應(yīng)當(dāng)引起法學(xué)界和司法界的深入思考。
更多勞動法內(nèi)容盡在勞動法律網(wǎng)http://www.zyufu86.cn
下一篇:惡意欠薪將獲刑